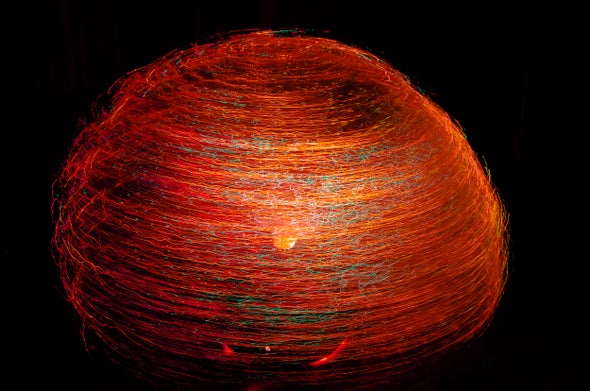在寻找外星生命的过程中,对外星智慧的探索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假定某些种类的生命会操纵和利用它的环境意图.和这种意图可能远远超出了支持基本的生存和功能。相比之下,对其他生命系统或生物特征的一般搜索,实际上都是关于进食、繁殖,以及(更确切地说)制造废物。
意图假设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天文学家珀西瓦尔·洛厄尔(Percival Lowell)就说服自己和其他人相信火星表面存在“非自然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与一种先进但濒临灭绝的物种从极地地区引水的努力联系起来。大约在同一时期,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提出了利用无线传输联系火星的可能性,甚至认为他可能已经从地球之外接收到了重复的结构化信号。近一个世纪以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也曾考虑过主动接触,并建议分割西伯利亚冻土带,以制造一个能被外星人看到的几何信号。
今天,寻求意图是由宇宙仍然合并的宇宙领域代表“technosignatures它包括对结构化电磁信号的研究,以及对有意操纵物质和能量的各种其他证据的研究外星人蜂师到工业污染,或夜间照明系统在遥远的世界里。
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难题。我们倾向于自动假定所有已知形式的技术都是“先进”生活及其意图的标志,但我们很少问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技术首先会出现?
我开始思考这个难题早在2018年,并基于外部地导致量化智能生活的更深层次信息该物种在我们称之为技术的内容中生成,使用,传播和编码 - 从洞穴绘画和书籍到闪存驱动器和云服务器以及维持器的结构。给出这个标签,我称之为“dataome”。这种破坏我们世界性质的一种结果是我们对技术的追求实际上是关于检测外星数据仪的检测。
这种重构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数据体可能更像一个生命系统,而不是任何一种孤立的、惰性的、合成系统。这有点挑衅(好吧,非常挑衅性)的想法是我得出更详细的调查我的新书的结论之一信息的崛起.我们的信息世界,我们的数据,最好是作为美国的共生实体(以及一般地球上的生活)。它真的是另一个“OME”,与与所有多细胞寿命的私密和不可指死的关系中存在的微生物不同。
因此,数据元在世界上的到来代表一个起源事件。正如我们认为,生物生命的起源,是由成功编码的自我传播,进化的信息在有机分子的基质中。数据体是一种成功的自传播编码,将信息进化到不同的基底,并具有看似不同的时空分布——将其大部分功能通过像我们这样的生物系统传递。和其他主要的起源事件一样,它涉及到行星环境的大规模重组,从能源的利用到大气或海洋的基本化学变化。
换句话说,我认为技术特征是数据体的结果,就像生物特征是基因组的结果一样。
这种区别似乎微妙,但重要的是。许多远程观察到的生物炎是生命的内部化学的结果;代谢副产品喜欢氧或者行星大气中的甲烷。还有一些是生命获取能量的结果,比如与光合作用相关的色素的颜色。所有这些特征都深深植根于生命的基因组中,最终,这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它们的基础和可能性,以及我们如何将这些标记从具有挑战性和不完整的天文测量中分离出来。
类似于生物创作者,技术知识必须植根于与生物生命共存的Dataomes(或者一次与生物学生命共存)共存。要了解技术的基础和可能性,因此我们需要识别和研究Dataomes的性质。
例如,数据组及其生物学生体系可能存在于不安的达尔文平衡中,其中每一侧的利益并不总是对齐,而共存为每个共存提供统计优势。这可能是评估关于其他世界的环境组成和能量转化观察的关键因素。我们自己正在经历我们的大气碳含量的增加,这些碳含量可能与我们的数据组的指数增长有关,但是组成变化对于保留我们的生物自我繁殖的条件并不好。
预测我们自己的数据体将把我们带到哪里,可以为其他地方的技术特征的规模和质量提供线索。如果我们只把技术特征看作是一种任意的现象集合,而不是达尔文主义的自然结果,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错过宇宙中正在发生的事情。